從小,我愛畫抽象畫。因為小時候口吃,講話總是「我———我———我———」個老半天,蹦不出話。惹來一身笑之後,我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裡,用抽象的線條和色塊,把梗在喉嚨裡的話語,一筆一畫,化為一幅又一幅的抽象畫。
左撇子變右撇子 我怪罪起媽媽來
剛開始,我拿著粉蠟筆,只是發洩情緒似的,使勁的圖畫,像隻失去理性的野獸,在圖畫裡亂撞,發出怒吼。我對著圖畫大聲說:「我———很———生———氣。」或者:「我———真———笨。」然後,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。
每一次,我用生命的線條練習發聲,總是這樣邊哭邊畫。但是,漸漸的,我發現自己在畫畫時,生命很流暢,可以不斷的和自己說話,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。
但是,為何面對外在的世界,我總是支支吾吾,猶如斷了線的琴弦無法發聲?長大後的我,從長輩口中明白,我所以口吃,很可能因為兒時從左撇子,被強迫換為右撇子的緣故。於是,我開始怪罪媽媽,總是背著畫具往外跑,從來不把畫拿給媽媽看,覺得她看不懂,也不了解我。
「哎呀,你們家的阿文好奇怪,總是一個人在樹下畫畫,畫了老半天,也看不出她在畫啥米碗糕?」每當有人質疑我的畫時,媽媽總是一笑置之。
她從不過問我畫甚麼,也不在乎我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大畫家,甚至連我為甚麼需要畫畫,她都不明白。她唯一為我做的,就是每一次我出去畫畫時,從後面追上我,然後給我一堆點心和茶水。
也許是自卑,我拒絕讀幼稚園。媽媽居然也沒強迫我。有一段很長的歲月,媽媽就讓我這樣一個人塗塗抹抹。我畫自己,畫生命的喜怒哀樂,也畫土地上所有的生命,然後拿著畫自言自語,像個「怪怪的小孩」。
老天爺愛開玩笑 口吃成演講選手
不知是老天爺開了我一個大玩笑,還是生命裡真的因為畫畫,找到發聲的出口?上了小學,我的言語,開始像我畫畫般線條流暢起來;而我的肢體語言,竟然像我畫的色塊一樣豐富。到了小學五年級,因為老師的訓練,我居然變成參加演講比賽的選手。生命裡不知不覺出現的轉機,終於讓我跨越了語言的障礙。
我的個性,從此豁然開朗。但在生命深處,卻突然擁有兩個不同極端的自己:究竟那個口吃不善言辭,喜歡安安靜靜的女孩是我?還是在人群裡很會說故事,可以滔滔不絕講話的人才是真正的我?
每次上台演講比賽時,只要想起那個內心裡,曾經因為口吃,說不出話來的自己,就很容易忘詞。因為那一個笨拙的我,是一個赤裸裸的生命,透射著那麼真誠的靈魂,讓在演講比賽中的我,覺得自己用受過包裝的腔調說話很虛偽。
複雜的社會、曲折的人心,漸漸讓我發現很多人很會說話,卻不說真話。個性耿直的我,反而比口吃不會說話的我,更容易受傷。然而,我也沒有完全喜歡那個會口吃的我,因為在人群裡,結結巴巴說不出話,會讓我覺得很丟臉。我因而變得心直口快,總是一股腦兒想把心裡的話說完,彷彿怕自己哪一天又會失去說話的能力。
我開始覺得自己活得好累。
媽媽說:「阿文,妳怎麼了?要不要出去畫畫?媽媽替妳準備點心。」我的心被重重的一擊,猛然有一種清醒。當我不再口吃之後,就很少再拿起畫筆畫畫,也不在畫裡和自己說話,而我的媽媽卻清晰的記得那樣的身影。
紅色色塊就是我 淚眼有當年小孩
我拿起畫筆,開始用線條和色塊,描繪屬於自己的畫像。從兒時、小學,到離家在外求學,畢業後成為老師,不同的階段、不同的身影,我用不同的色塊層層疊疊勾勒出自己;但是,腦海裡最鮮明、最難以忘懷的,總是那一個關在房間,很孤獨的、很真誠的,因為口吃,努力練習發聲的自己。
我用紅色的色塊,代表那一個生命中的自己,同時用這樣的紅色,覆蓋所有的畫面,覆蓋不同階段的自己。
有些畫面,保留血淋淋的紅色;有些畫面,則因顏色矛盾交雜,而顯得骯髒污穢。
我突然想放聲大哭,因為我看見的,是一個從很多矛盾衝突當中,血淋淋活出來的生命,一個無可迴避,卻真實深刻的生命。
從那一次以後,我發現自己的心靈,藏著一枝無形的畫筆。當我在人群裡活得很累的時候,就用那一枝畫筆,開始畫畫。每次輕輕地畫出那個口吃、很笨拙,卻很真誠的身影時,我總會會心一笑。那是我,最喜歡的自己,從來沒有消失。
我突然好想好好畫一幅畫給媽媽看,因為她從來沒有真正看過我的抽象畫。我居然到這麼多年才明白,媽媽當年給我的,是一個可以盡情畫畫的「空間」。而我,卻一直在心裡怪她害我口吃。
今年返鄉探親時,我畫了一幅畫送給媽媽。畫中的媽媽,有大大的肚子,孕育了五個小生命。五個小圓球,從媽媽的肚子裡,由內而外散發一種光芒,穿透整個家,和媽媽融為一體。
我有點緊張,不知媽媽究竟懂不懂我畫的抽象畫?
六十幾歲的媽媽老了,戴著老花眼鏡,努力看著我的畫,鼻子差點頂到我畫的粉彩上。媽媽笑著說:「妳畫得很好啊,只要妳快樂,畫甚麼都好。」
我感動得紅了眼眶。在淚眼模糊中,看見那個曾經關在房間、口吃的小孩,打開門,擁抱媽媽的愛。【黃淑文】
這個部落格打算有效的整理口吃資料、口吃肇因、口吃改善、口吃心理學、口吃經驗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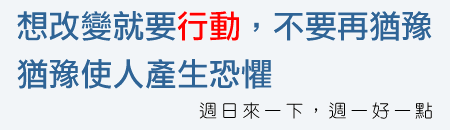

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